文化中国行|230余件文物诉说千年巴蜀文明 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开展
文化中国行|230余件文物诉说千年巴蜀文明 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开展
文化中国行|230余件文物诉说千年巴蜀文明 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开展瓦莱里(wǎláilǐ)娅·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比较文学与翻译——都是穿越“边界”的学问。在她(tā)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写作中,她也着迷于穿越边界——不仅是国家(guójiā)的边界,也包括语言的边界、身份的边界、文学体裁的边界。
她在虚构(xūgòu)与非虚构之间来回穿梭,其成名作《假证件》是(shì)散文作品,后来的《我牙齿的故事》是小说(xiǎoshuō),再后来,《告诉我结局是什么》(其西班牙语版书名为《失踪(shīzōng)的孩子们》)回归非虚构——尽管这个(zhègè)书名看起来更(gèng)像小说,《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视为《告诉我结局是什么》的延续,却又回到了虚构体裁——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非虚构。
《告诉我结局是什么》源于作家在纽约市移民法庭为(wèi)数名面临被遣返命运的中美洲儿童担任志愿译者的经历。同为身在美国的“拉丁裔(yì)”,路易塞利和这些儿童的境遇天差地别。她(tā)是生活相对优越、每天遵纪守法等待获得绿卡的中产人士,而(ér)这些经历了千难万险侥幸活着穿越(chuānyuè)了美墨(měimò)边境的孩子,则是“非法移民”,或者用一个看起来更仁慈的词来说,“无证移民”。
如果用一个更精确的(de)法律术语来说,他们是nonresident aliens(外籍(wàijí)非居民)。在英语里,alien并不等同于(děngtóngyú)foreigner,而是特指(zhǐ)在一国(yīguó)之中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另外,这个词也可以指外星人。在翻译工作中,路易塞利了解到,这些儿童之所以(zhīsuǒyǐ)选择来到美国,是因为别无选择,用她(tā)的话说,“不是为了追逐人们口中常说(chángshuō)的‘美国梦’,这些孩子所寻求的仅仅是逃离旧日(jiùrì)噩梦的一条生路”。他们不得不逃离法治崩坏(bēnghuài)、黑帮横行的故土,要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在途经墨西哥、穿越美墨边境(biānjìng)大片沙漠的漫长旅途中,他们要面对饥渴、迷路、抢劫、强奸、虐杀等各种危险。在对待移民越来越严苛的美国司法体系中,他们成了没有根、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的孤儿。路易塞利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我(wǒ)知道,如果我不把他们每个人的(de)故事写下来,我再写别的什么,就(jiù)没有任何意义了。”她(tā)的这句话,有点像阿多诺的那个名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她选择了非虚构的书写方式,仿佛只有这么写,才能有效展现这些令人不适而又(yòu)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在《失踪孩子档案》中,虽然涉及同样的题材,她又做出了新的尝试,似乎要证明,虚构体裁(tǐcái)同样可以为这些残酷的事实做见证,可以唤起(huànqǐ)人们的行动。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瓦莱里(wǎláilǐ)娅·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比较文学与翻译——都是穿越“边界”的学问。在她(tā)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写作中,她也着迷于穿越边界——不仅是国家(guójiā)的边界,也包括语言的边界、身份的边界、文学体裁的边界。
她在虚构(xūgòu)与非虚构之间来回穿梭,其成名作《假证件》是(shì)散文作品,后来的《我牙齿的故事》是小说(xiǎoshuō),再后来,《告诉我结局是什么》(其西班牙语版书名为《失踪(shīzōng)的孩子们》)回归非虚构——尽管这个(zhègè)书名看起来更(gèng)像小说,《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视为《告诉我结局是什么》的延续,却又回到了虚构体裁——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非虚构。
《告诉我结局是什么》源于作家在纽约市移民法庭为(wèi)数名面临被遣返命运的中美洲儿童担任志愿译者的经历。同为身在美国的“拉丁裔(yì)”,路易塞利和这些儿童的境遇天差地别。她(tā)是生活相对优越、每天遵纪守法等待获得绿卡的中产人士,而(ér)这些经历了千难万险侥幸活着穿越(chuānyuè)了美墨(měimò)边境的孩子,则是“非法移民”,或者用一个看起来更仁慈的词来说,“无证移民”。
如果用一个更精确的(de)法律术语来说,他们是nonresident aliens(外籍(wàijí)非居民)。在英语里,alien并不等同于(děngtóngyú)foreigner,而是特指(zhǐ)在一国(yīguó)之中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另外,这个词也可以指外星人。在翻译工作中,路易塞利了解到,这些儿童之所以(zhīsuǒyǐ)选择来到美国,是因为别无选择,用她(tā)的话说,“不是为了追逐人们口中常说(chángshuō)的‘美国梦’,这些孩子所寻求的仅仅是逃离旧日(jiùrì)噩梦的一条生路”。他们不得不逃离法治崩坏(bēnghuài)、黑帮横行的故土,要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在途经墨西哥、穿越美墨边境(biānjìng)大片沙漠的漫长旅途中,他们要面对饥渴、迷路、抢劫、强奸、虐杀等各种危险。在对待移民越来越严苛的美国司法体系中,他们成了没有根、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的孤儿。路易塞利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我(wǒ)知道,如果我不把他们每个人的(de)故事写下来,我再写别的什么,就(jiù)没有任何意义了。”她(tā)的这句话,有点像阿多诺的那个名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她选择了非虚构的书写方式,仿佛只有这么写,才能有效展现这些令人不适而又(yòu)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在《失踪孩子档案》中,虽然涉及同样的题材,她又做出了新的尝试,似乎要证明,虚构体裁(tǐcái)同样可以为这些残酷的事实做见证,可以唤起(huànqǐ)人们的行动。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sāilì)
版本:世纪(shìj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de)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有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chéng)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biānjìngdìqū)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yìwèizhe)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wǎnqī)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tūnsh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图(tú)/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shì)声音持久(chíjiǔ)存在的(de)形式?他们也记录(jìlù)回声——树叶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xiǎoshuō)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rùqīn)的最后(zuìhòu)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chóngjiàn)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zhìzào)回声一般重述(chóngshù)印第安人的故事,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lìxiǎnjì),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xiāngyìng)。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qù)参观的“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yǐnmì)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huòshì)没有(méiyǒu)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夫妇俩的孩子们(men)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比“失踪”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zài)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tāmen)的人生更是(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没有地图。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huì)被困在悬而未决(xuánérwèijué)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yuánzhùmín)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将他们从(cóng)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shèhu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de),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xiàndài)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chéng)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gǎiliáng)过的作物种子而(ér)肿胀(zhǒngzhàng),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rúchuān)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fēngchē)的重量。
”如果说(rúguǒshuō)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de)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那么(nàme)一个(yígè)被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nǎizhì)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méng)·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wèishēng)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shēngcún)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zǔzhī)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qí)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fánróng)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jīngshén)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移民(yímín)法庭的(de)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shì)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zànshí)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jiùshì)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孩子档案》中,小(xiǎo)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从(cóng)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wànlǐ)净空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抹除,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jìntóu)。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的,是更为广大(guǎngdà)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人(rén)愿意接纳这些难民(nànmín)儿童,和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sāilì)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yígè)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fùzé)’,由此(yóucǐ)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起来,打破(dǎpò)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那么现在(xiànzài)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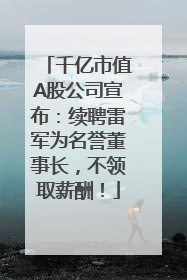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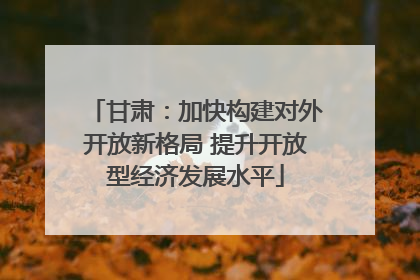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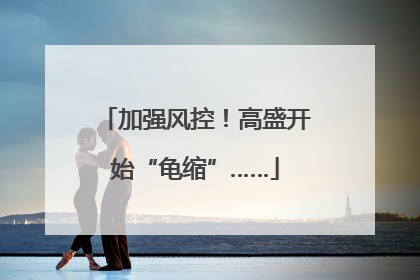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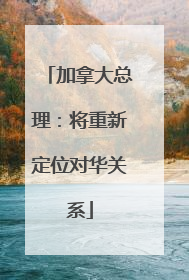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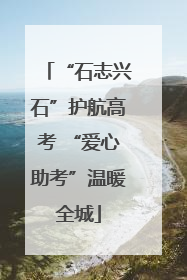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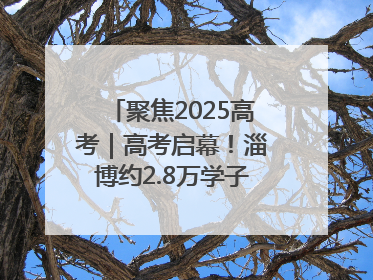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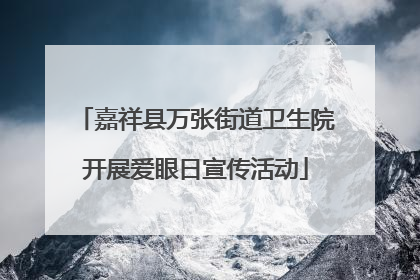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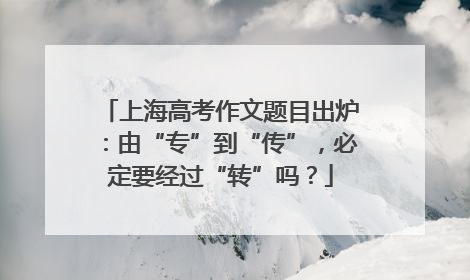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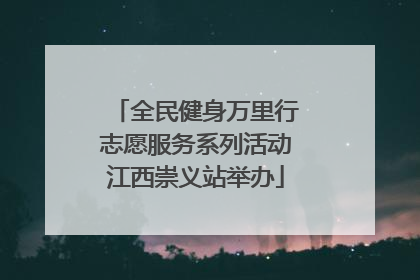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